黃聲遠,1963年生於台北,美國耶魯大學建築學校碩士。1994年移居宜蘭,從土地與生活出發、展開建築創作生涯,他主持的「田中央工作群」匯集宜蘭和台灣各地的有志青年,擺脫學院派的知識框架,從環境感知與自然系統的理解中,自在且自主地梳理出屬於宜蘭在地的空間環境創造,啟發了許多建築人回歸土地和從環境的節奏中,找尋建築與人緊密連結的本質,代表作有:羅東文化工場、櫻花陵園、雲門劇場等。
黃聲遠2006年獲選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2006年、2018年田中央獲選代表於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參展,2015年應邀在東京「間美術館」展出,並從2016年底起赴歐舉辦巡迴展,這是台灣建築師首次獲邀至歐洲巡展。2014、2017年兩度獲頒「遠東建築獎台灣傑出獎」,2017年獲日本「吉阪隆正賞」,是首位非日籍建築師獲獎。
阿堯:
謝謝你送我的小說,帶著我翱翔。隨著細膩文字的起伏,似乎重溫你二十年來的成長。是的,我們都一起走過二十年了。
想起人生中鼓舞過我的那些貴人,他們是不是也曾經為我緊張?最近想寫些感謝的文字交給國藝會,努力了半天,卻怎麼看都覺得味道不對,強度不足。
倒是這次國藝會邀的格式裡,還有一部分叫作「個人大事紀」(我知道你會覺得怪怪的),讓我想起來好像很少和你說起我小時候的故事:如同那個時代很多勇敢的父母一樣,黃爸黃媽拎著妹妹和我搬過八次家…
那是一段身體在空間中歷練衝擊的扎實歲月。在城市裡,我必須要在很快的速度內組合拆解別人以為的秩序;出了城,在一片廣袤活生生的風景裡,可以聽見海浪、風沙、落葉和蝴蝶起飛。
於是當我在三星鄉的大山大水遇見你的時候,有一種久別重逢的感覺。我知道還是國中生的你,安靜是為了什麼,也知道讀書考試困得了你一時,卻擋不住你的天分。
其實我的初中生活有些才是不堪,被以成績分類,糊塗去欺負沒有出口的同學;高中更是荒謬,在一片抓施明德「叛亂犯」的宣傳海報中,大家還高高興興地排練大會操,拍進看電影前唱國歌的片頭。
你知道我一九八九年出國留學,錯過了九○年遍地盛開的野百合…
於是我體會到能夠一直做自己喜歡的事是重要的,每一次碰上足以衝擊信仰的重大挫折,我也是需要時間來進入那個可以專注等待的平行時空。你記得二○○五年宜蘭變天那晚吧,直到第二天中午,當我拾起桌上的模型,才有了支撐力重新振作起來。那時候好多人勸我去香港、去台中做點別的。好在我只聽得進親愛老婆的溫柔提醒:「建築和宜蘭這片土地,明顯地是你的最愛。」
不能對不起阿欽,不能對不起你們的信任,「不容許便宜行事」也許是我靈魂裡最硬的那塊骨頭。
大地之美,愈鍛鍊愈可以看出不必存在的雜質。這塊土地,一定要說自己的話。
從那天起,我有了一步一步邀請全世界來呵護她的念頭。
來到宜蘭二十五年,學會把別人的夢當作自己的事。這裡有很多人願意把日常的點滴都當作是偉大的工作。
事實上也是,社會永遠透過支持自由的作品,表達真心的期望。每一個人相信的可能,就會是世界的未來。
今天是你考上建築師的大日子,也是更多試煉的開始。希望你兩個可愛女兒長大的時候,台灣不再還是不願分辨美醜的社會。
黃聲遠
二○一八年初,宜蘭田中央
黃聲遠的匠藝
〈自由城市〉
莫忘初衷
落腳在台灣的宜蘭,
我們終於可以在鄉村工作(開會),
晚上再回到城市裡睡覺了(有7-Eleven)。
我們徜徉田園但更是喜歡城市——
一種穠纖合度自給自足的風情城市。
這種城市和台北想要的不同,
和深圳想要的可能也不一樣:
她要可以讓小孩安全地騎車,
進出政府機關像穿過自家後院,而且,
發生過的故事,以後還都找得到痕跡。
試著只做三十分鐘車程以內的工作,
什麼都該做,什麼都得學,
不忘建築本來可以為別人做很多事情。
累積得愈久,
從生活細節往上架構的都市計畫才不會讓都市一直擴大。
風情城市的自豪,就是讓人們得以隨時自在地選擇進城還是出城。
年輕時候的玩笑:「找一個值得落腳的地方,在那裡,忙得不亦樂乎的人還很喜歡小孩,就算是建築師也不會害怕結婚……」
這是一個放鬆的城市,
一個因為慢,所以多元,
一個因為慢,才能了解,
真正的自由不是離開,而是可以選擇留下。
不必跟著別人,
不必依賴消費。
這是我們的城市,
我們叫她——自由。
(二○○五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年展,黃聲遠)
赫菲斯特斯的建築師形象
希臘奧林帕斯十二位主要神祇中,匠神赫菲斯特斯(Hephaestus)是較少被注意到的一位。赫菲斯特斯長相醜陋且跛足,與長相皆俊秀完美的諸神,成強烈對比,是諸神中的異數。但赫菲斯特斯卻廣受眾神敬重,因為他匠藝精湛,奧林帕斯山上諸神所住的精美宮殿,皆由他所建。除了是位傑出的建築師外,赫菲斯特斯也是巧匠,精通金屬和珠寶製作,也造家具和武器。眾神只要得到他協助,總能神力大增,如第一勇士阿基里斯(Achilles)的無敵盾牌就是由他打造,藉此攻陷特洛伊,扭轉了戰局。荷馬在《伊利亞德》(Iliad)第十八卷後半,以極長的篇幅,以這個無敵神盾的製作過程與各部細節的詳細描寫,竭盡所能地讚揚赫菲斯特斯的藝術成就。
赫菲斯特斯是建築師最早的形象,我們今日所稱「建築」(architecture)一詞,即出於古希臘時期。在這個形象中,建築師與匠人並無二致。完美的建築出自畸形的身體,意味著完美與不完美之間可以流走互通,之間並無截然二分的界限。而這個完美與不完美之間界限得以突破,乃精巧的製作所致。是「製作」(making)讓不完美的現實得以被克服,趨向完美。因此古希臘時,製作並非指一般性的製作,而是指人們透過長時間專注,想盡各種辦法精益求精,堅持品質毫不妥協的製作。
精巧製作過程必定包含著高超技術的運用,而技術來自知識的應用。像赫菲斯特斯這樣的匠人,崇尚的知識是透過親身經驗獲取的「實作知識」(working knowledge),而非抽象、未經身體力行檢驗過的知識。「實作知識」來自匠人(也就是建築師)一生不停地專注製作以及磨練技能,在這樣的身體經驗裡所累積下來的知識。因此匠人的知識也是「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因為經驗是記存在身體裡的,很少能被語言化,他人唯有透過口授並且不懈地跟著身體力行,才能獲致。但這並不是說匠人僅封閉於自己的工作坊之中,以自己累積下來的知識為唯一知識,匠人一樣好奇於工作坊以外的知識,只是這些外來的知識若非經過親身驗證為合用,是不會視為與自身有關,也就是有用、真正的知識。這是優秀匠人的知識本體論。古希臘文中,技術寫為「techne」,隨後拉丁文譯為「ars」,即今日「art」(藝術)的來源。這樣的詞語演化說明,在古代世界,藝術領域與技術領域並無分別,與今日我們認知的藝術這個詞語的內涵,不盡相同。以今日的語境來說,「techne」或許比較適合稱呼為「技藝」。
然而,技藝並不會自動轉變為知識,其間必須經過反省思維,也就是一種桑內特(Richard Sennett)所描繪的「手腦對話」的過程。在《匠人》(The Craftsman)一書中,桑內特長篇論述了為何康德(Immanuel Kant)會說出「手是心靈的窗戶」這句話:腦指揮手進行製作,而手在進行製作的過程,也會反過來指導腦該如何思考。手的製作,不僅是解決問題,同時也發現新的問題,為解決這個新的問題得到了新的解答,而新的解答又引出更新的問題,在獲得解答,如此一路衍生,就是精益求精,也就是技藝得以不斷發展的過程。這也是為何「製作」一詞在古希臘文為「poiein」,它也衍生了詩(poetry)這個詞語。詩人作詩,也是一種製作。詩,就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指出的,為詩意的語言,來自思維令語言的純粹化,詩與思因此不可二分。像赫菲斯特斯這樣的匠人建築師,不是一般所認知的技術者,而是一個懂得透過製作去思考的人。因此技藝為製作與思維的結合,製作的過程包含了思考。而思維是一場生命之旅,偉大匠人終其一生實踐的是製作與思維結合之旅,在製作與思維互用的過程之中,技藝得到不斷的提升。
在赫菲斯特斯的匠人建築師形象裡,也說明了專業自主性的由來。在製作這個王國裡,赫菲斯特斯的自由,除了來自他擁有一般人無法獲致的匠藝外,也來自他的匠藝提升了眾神的生活水準,博得公眾的尊敬。在希臘古風時期(Archaic Greece),也就是赫菲斯特斯故事被傳頌的時代,稱呼匠人的詞彙是「demioergos」。這是個複合詞彙,由「demio」(公共的)和「ergos」(生產性的)組成。當日一首讚詩曾如此稱頌赫菲斯特斯:「繆斯嘹亮地歌頌著,因心靈手巧而著名的赫菲斯特斯。他跟隨著眼睛明亮的雅典娜,把各種匠藝傳遍全世界。人們原本就像野獸那樣住在山洞裡,但如今他們向名聞遐邇的赫菲斯特斯學會了許多技術,所以它們整年都能夠在自己的房子裡過著祥和的生活。」這段神話說明了製作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連續關係。因為向赫菲斯特斯學得建造房屋的技藝,人類才得以終結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有了和平與文明生活。赫菲斯特斯匠藝來自天生的才華,但他卻讓匠藝超越了它自身,貢獻給共同體的組聚和維持,同時也讓赫菲斯特斯獲得了自由。
建築即為製作
黃聲遠正是這樣一位赫菲斯特斯式的建築師。雖然有著美國一流大學的建築碩士學位,也曾在美國著名建築師Eric O. Moss事務所工作,並在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教授建築,對於西方當前時興的建築創作並不陌生,但黃聲遠並不著迷於這些外來的抽象建築知識,而是如一名優秀的匠人,回歸自身,從自己的經驗來累積匠藝。自從一九九四年定居宜蘭以來,黃聲遠帶領著田中央,一起在宜蘭創作了超過五十件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絕大多數,都是可供一般人自由使用的公共建築和公共空間,星羅地散布於宜蘭平原之中,一方面與各式在地地景緊密嵌合在一起,提升了宜蘭人生活環境的品質,另一方面也改塑了宜蘭地景風貌,轉變了宜蘭建築的形象。黃聲遠的多產、活力和獨特,使得在建築界,當大家說起宜蘭,就想起黃聲遠和田中央,彷彿黃聲遠是個土生土長的宜蘭人,少有人記起黃聲遠原來是個不過入住二十餘年的外來移居者。
正是在這些公共空間營造的過程中,黃聲遠和他的同事累積了良好的專業聲譽,也形成了田中央獨門的「實用的隱性知識」。黃聲遠二十餘年在宜蘭創作的過程,從某個角度來說,就是在書寫一本《宜蘭之書》,而這本黃聲遠的《宜蘭之書》的首部,具體呈現在由日本TOTO出版的英日文作品集《Living in Place》。書中黃聲遠將自己的作品,分為四個「領悟」來進行作品自我分析,包括「與時間做朋友」、「認真地生活在山海水土之間」、「大棚架和地景參考線」,以及「記得身體、忘記時間」。
「領悟」,意指是在製作完成之後才理會到的,非事先就預知的。如同黃聲遠在以「維管束」計畫為例,闡述田中央創建以來的工作方式時所表達的,「(維管束)並非是執行的計畫,而是一邊做一邊釐清的想法」。這是一種對自己匠人式行事方式的自覺,理解到這是自己工作不斷進行過程中,對於身體經驗的暫時性的歸納整理,所以他才說「沒有辦法很有『順序』、很有『結構』、很『清晰』,因為這一切都是重疊發生,而且還不斷在修改進行中」。
一九九○年代末似乎是黃聲遠匠藝累成的第一個關鍵時刻。一九九五年,當他透過生活在宜蘭以及規劃設計「社會福利館」,開始能較深入了解宜蘭地景紋理背後的意義時,黃聲遠注意到鄰近的鄂王社區。透過不斷梳理該地區的紋理關係,他逐漸悟識到社福館的新建,不僅會為鄂王社區注入新的活力,也會帶來無可挽回的破壞。面對這個兩難局面,一般建築師大概只會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而專注於自己負責的新建築的建造。但黃聲遠選擇面對這個困境。在沒有任何人付費委託下,他自行為這個社區環境的改造,企劃一連串行動方案。這些方案經過多次擴展和修正,近十年後被集結命名為「第一維管束」,長度約五六○公尺。黃聲遠當時或許感覺到,這些仍欠缺成熟的行動方案要實施困難重重,但「第一維管束」真的被實施了,只是花費了田中央十三年的光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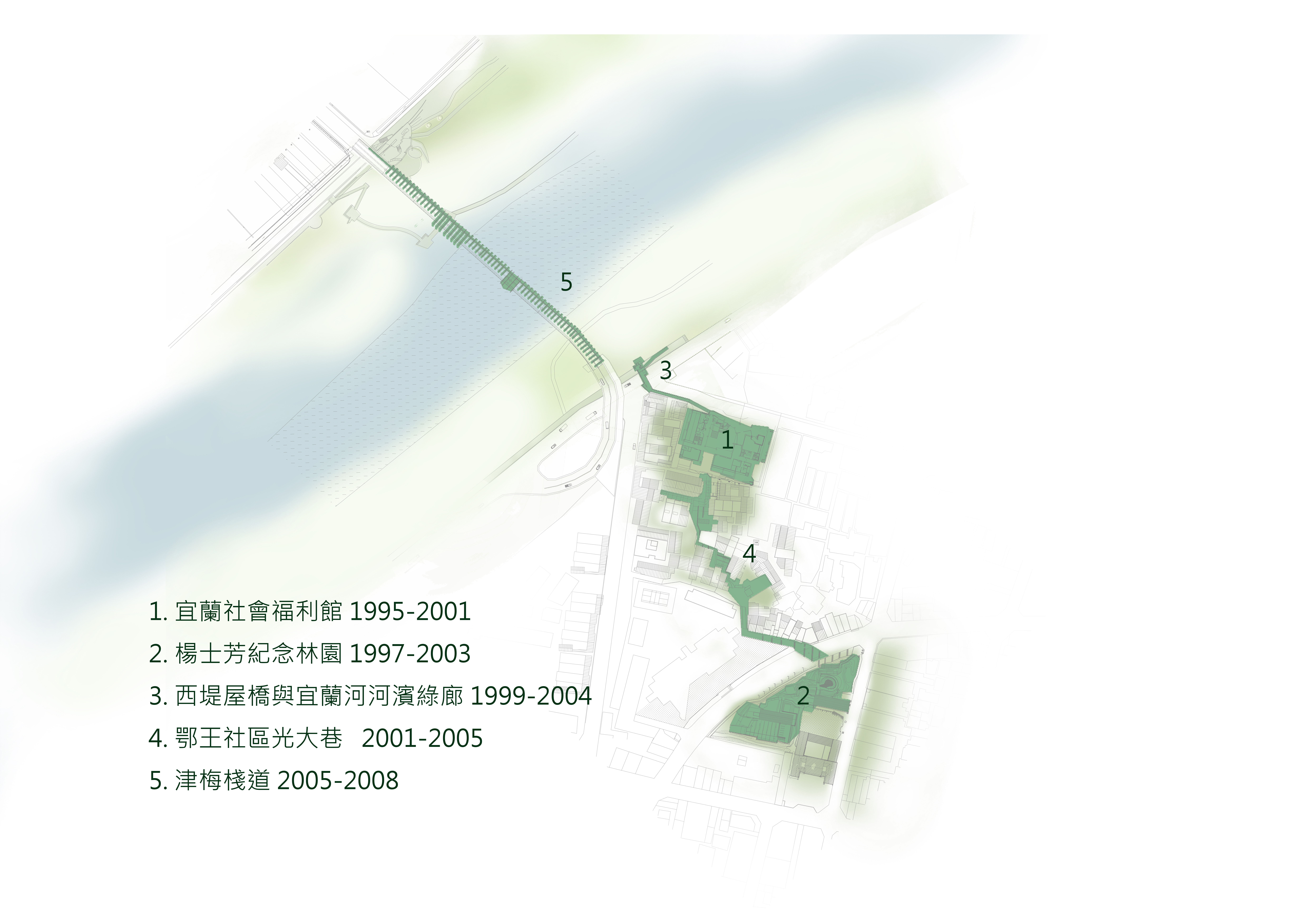
黃聲遠當時發展出來的梳理地區紋理關係的方法,除了現時性的現況調查和居民訪談外,也包括歷時性的地區過往歷史調研,最後這些歷史調研的結果被逐一重疊在現況圖上,並被呈現在大尺度模型上。而這些行動方案有一個模糊的目標,就是讓鄰近河堤外的宜蘭河空間,能夠納為社區空間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被快速道路和河堤切斷的鄂王社區和宜蘭河之間,重新建立連結,讓自然進入社區,補充社區缺乏的、公園般的大型開放空間,而社區居民能夠進入自然、照養自然,讓兩者互蒙其利。
其中最具體的計畫,是從社福館建立一條後來被稱為「西堤屋橋」的步行橋到堤外。然而當時並沒有經費可以興建這座橋,堤外宜蘭河也仍是荒地一片,民眾在此丟棄大型垃圾,光禿禿的水泥堤防沒有任何生氣。而在朝西北連接宜蘭河的期待中,反倒東南方先出現了機會。一九九七至二○○三年間,田中央建造了「楊士芳紀念林園」,這個公園富有舊城城牆意象和蜿蜒園林之美,將「第一維管束」延伸到到碧霞宮,而碧霞宮和廟前的城隍街是舊城內西北地區的生活中心。楊士芳紀念林園的建造,也讓黃聲遠更加確定光大巷改造的必要性,但和西堤屋橋一樣,它仍然是想像中的計畫,沒有人知道是否能實現?雖然如此,在沒有委託的情況之下,田中央自發地與光大巷居民進行溝通,端著大模型挨家挨戶地說明,認真地考慮每一戶居民的需求,比如看似微不足道的積水問題的解決方案等。光大巷這個古地名,也在此溝通過程中,決定被回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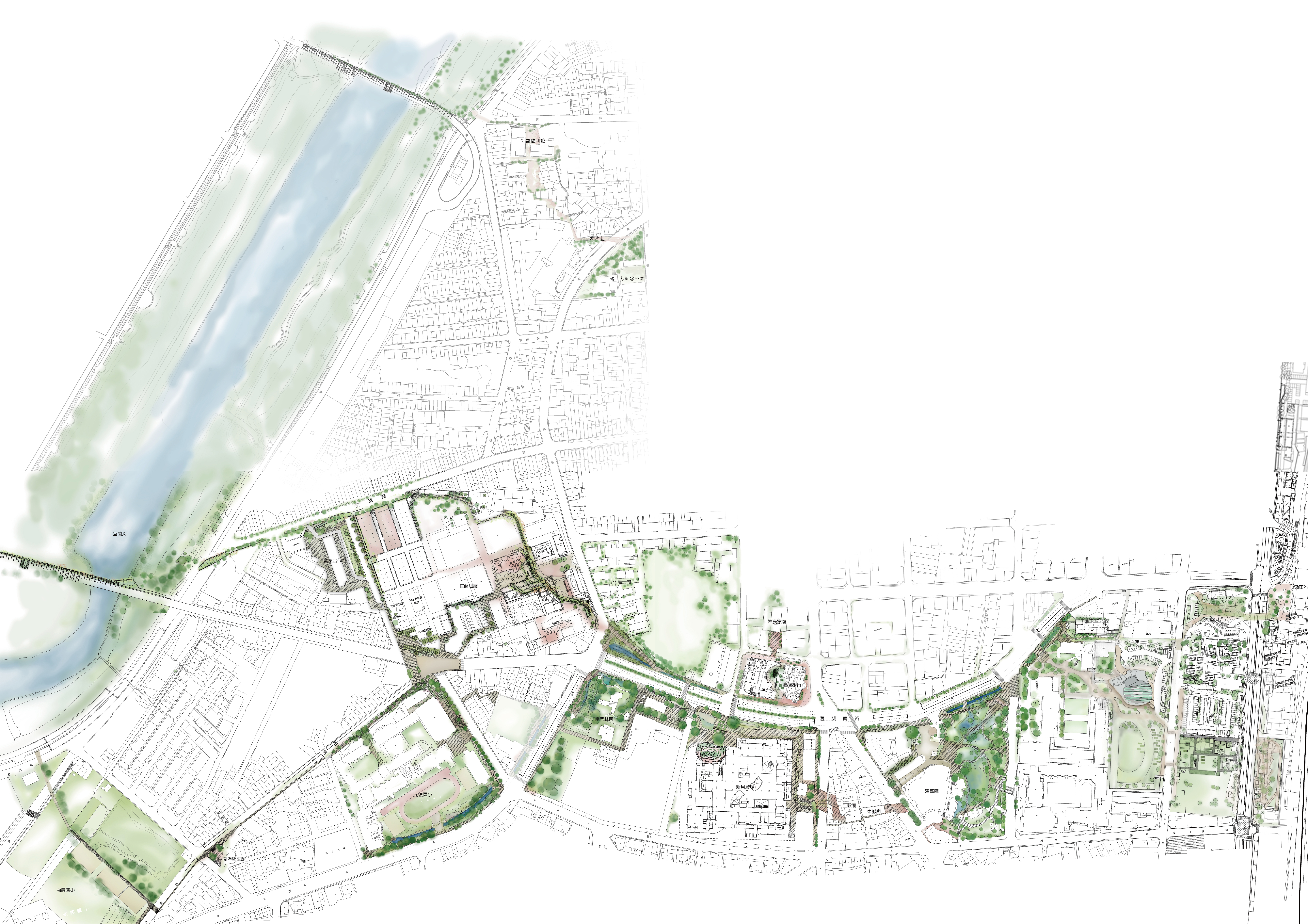
一九九九年,就在社福館開工後不久,為了挽救經濟危機,中央政府突然宣布實施「擴大內需方案」,啟動大筆經費支援地方建設。「西堤屋橋」因為設計好馬上可以建設,順利獲得建造經費,同時宜蘭河也進行綠化改造。兩年後,因已取得居民共識,光大巷的改造也開始動工。此時,田中央開始研究興建一條跨越宜蘭河到對岸的步行橋,讓人們可以安心步行過河,並有機會在過橋之際領略綠化後的宜蘭河之美。幾經試驗和思索之後,田中央提出不另建橋,而是在原本僅供車行的慶和橋的側邊,以輕巧的結構和極低的經費附掛出一座「津梅棧道」,於二○○八年完工。就在第一維管束逐漸發展成型之際,二○○四年起黃聲遠開始嘗試以舊城南路為中心,發展出後來被稱為「第二維管束」的大型生活廊帶,長達一‧四公里,目前已有十餘個行動方案被完成。「第三維管束」則於二○○九年開始進行。除此之外,於一九九九年開始規劃設計的「羅東文化工場」,也歷經十四年才完成,在此不斷受挫的過程中,田中央也展開梳理羅東城鎮紋理的工作,最後提出羅東「小鎮文化廊道」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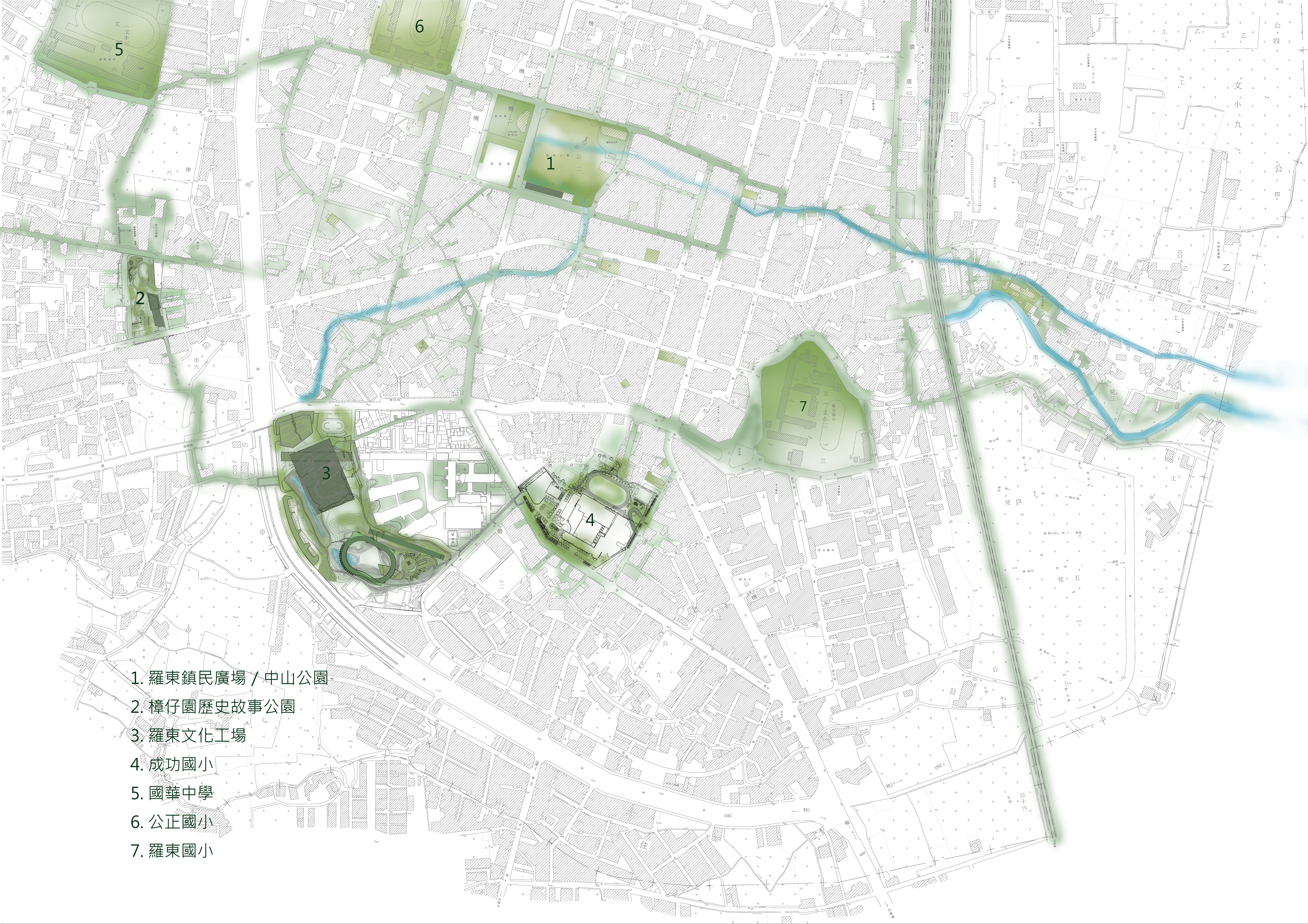
「第一維管束」是黃聲遠匠藝發展的第一塊試金石。在這裡,黃聲遠將梳理地區紋理關係視為設計的第一要務,是因為黃聲遠理解「最小力量」的智慧。也就是,嘗試著以最小的行動─只要動用最少的資源和面臨最小的阻力,巧妙地調整既有的紋理關係,和加入不可或缺的微量新元素,達成最大效力的環境改造,目的在為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活力,好在面對未來時能有更好的適應力。這也顯露了他對於建築師工作的特殊看法:建築師的主要工作在於改造環境整體,而非僅專注於單一建築物的建造。他將建築當成一種大型的公共空間製作,所以必須把現場當作匠人作坊,而其主要使用材料,也非可送進作坊的原料,而是已存在於現地的紋理關係。理解紋理並善用已有的資源,是黃聲遠邁向創作自由的第一步。
大尺度模型的應用
大尺度的模型製作,是黃聲遠發展其匠藝的另一項重點。這些模型多以1:50和1:100來製作,在製作1:50和1:100模型之前或同時,還伴隨著許多更小或更大比例尺模型的製作。因此田中央宛如一座模型製作工廠。而這些模型並非設計過程中或設計完成後的展示用模型,而是一直處在修改中的「工作模型」。田中央的設計流程,以模型製作為中心,各式的繪圖,包括施工圖,都是對模型的闡釋和說明。模型的製作既耗時又耗人力,加上攜帶不便,一般事務所少將模型視為主要設計工具,更何況大尺度、動輒數公尺以上的模型。但為何田中央堅持於此呢?
大尺度模型的好處之一,是它讓設計技藝的發展與累積,變得非常直接和容易。建築設計並非設計者無中生有的創造,在設計的過程中,設計者必須接收許多資訊,也必須判斷這些資訊何者是關鍵的,並以創造性的方式將這些關鍵資訊整合,並轉化為有美學感受的空間呈現出來。這是一種內化(embedding)的過程,內化讓接收的資訊和身體的實作得以合而為一。大尺度模型的製作,對於這個內化的過程助益頗大,因為它能直接將整合的成果展現出來,讓模型製作者、也就是設計者,立即看到而能馬上判斷是否進行修改。這正是一種典型的匠人「手腦對話」的過程。而成熟的內化,仰賴不停地修改,也就是不厭其煩地、反覆地練習,製作者身體經驗深入到設計之中,匠藝逐步被磨練出來。因此田中央大尺度模型上充滿拆補挖填、新舊雜陳的痕跡,正是藉由不斷修改鍛鍊其思考和製作合整為一的紀錄。繪圖也可以發揮類似的作用,但它因為每張圖都是空間整體的局部和二向度的,要具現成三向度的空間,必須仰賴觀圖者看圖之後綜合起來的投射力,這樣不但間接,也容易發生錯誤還難以察覺。
大尺度模型的直觀性,也對設計所需的直覺性操作有幫助。田中央的大尺度工作模型,是寫實性的,從事務所剛成立時,黃聲遠就要求大尺度模型必須以盡量接近實際被建造出來的情況來製作。這要求一方面是因當時黃聲遠自覺自己的建造經驗有限,想要藉此少犯錯;另一方面,從之前的設計經驗中,黃聲遠也認識到,大尺度模型容易操作出與環境之間的細膩關係,比如細微的轉折、材料的協調,和有利於社區生活發生的零碎但讓人感到輕鬆的空間。黃聲遠總是在全觀性的、大敘事的設計概念和局部的、小敘事的嵌入中,徬徨不已。他清楚地意識到,雖然清晰的整體性設計概念是重要的,因為它會賦予所有空間一個架構,但這總會冒著和既存紋理格格不入的危險。為此,黃聲遠對於設計概念保持著警覺,並藉由建築物邊緣與周圍環境對話所創造的空間,由外而內地削減設計概念的破壞力,有時甚至直接引入既存環境的紋理去對抗設計概念的完整性。大尺度模型能忠實地實踐黃聲遠這些想法,因為設計概念與既存紋理的衝突,在大尺度模型上呈現得較為清楚,同時要在大尺度模型上操作出與周圍環境共舞的個別性空間,要比小尺度模型容易得多。在操作這些個別性空間時,直覺就變得很重要,因為它需要的是直觀地、靈活地因地制宜,而非基於設計概念跟循某個原則。正是用手做出這些大尺度模型的過程中,讓具有批判力的直覺與跳躍思考和理性的設計概念辯證,創造了田中央作品的獨特性。
大尺度模型的另一好處,是便於溝通,幫助建立真正共識。大尺度模型因為寫實具體,可直觀思考,讓設計討論變得容易,建立起來的共識是較牢固的。田中央內部的設計討論,都是環繞著大尺度模型進行,與外部顧問的討論會議,如結構顧問和機電顧問等,也是如此。對於非專業的人也有類似效果,如官員和居民,可以從寫實模型中,具體看到公共空間的未來,以及它的建造將產生的影響;而田中央也因此能具體感受到使用者的憂慮與不安,進而調整設計來消除這些困擾,降低公共工程常產生民怨的情況。
大尺度模型也被田中央用來模擬營造過程,以便對於施工方式進行預判。最後,大尺度模型會被搬到工地,做為對現代營建體系缺陷的彌補。現代營建體系依賴建築師繪製的施工圖,做為營建操作的起點。先不論經常因過於龐多複雜而錯誤百出,或是因建築師不諳工法而致施工困難,這些施工圖以施工過程的勞動分工來繪製,本身就帶有令人見樹不見林的缺點。營建工匠經常是在無法窺見建築整體的情況下,進行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不但易生糾紛影響營建品質,也讓勞動異化。大尺度模型呈現在工地,工匠可以看到整體與細部,理解到自己操作的工項與整體的關係,讓異化之害降低。更重要地,大尺度模型容許一種在匠人製作時、最需要的身體的直接連結感的產生,營建因此不僅是體力勞動,而可以回到匠藝本身的追求,這是平面型的施工圖所遠遠不及的。
透過建築了解自身
大尺度模型的製作,對於田中央來說,是其建築營造繁複過程的綜合體,它整合了對環境脈絡的批判性梳理、設計技藝的發展、手腦對話、直覺的運用、利於溝通等,並培養了對於營建過程投射的能力。大尺度模型對於田中央來說,不僅是一項有效的工具,也是其建築匠藝的象徵。這個象徵還指出田中央工作時一項至關重要的核心:合作,以及環繞著合作進行的反思。
合作是赫菲斯特斯神話裡不存在的元素。做為一位神祇,赫菲斯特斯的匠作,是不需要與人合作的。荷馬描寫赫菲斯特斯為阿基里斯製作無敵神盾時,不需要任何的助手,只需要對風箱發出開始工作的指令,風箱就能迎合赫菲斯特斯的願望,操控爐火,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條。他還有黃金鑄成、心意相通的侍從協助,這些侍從形如少女,能思考說話,並具有高超的做事技能。然而在現實世界裡,少有建築師不與他人合作而能完成建造,但合作常卻令建築師痛苦不堪。
田中央大尺度模型的製作,通常就在辦公室空間的中央,四周被個人的工作空間所環繞。這樣的空間安排,反映了黃聲遠設定大尺度模型做為田中央工作流程裡的核心,雖是起因於功能,但也暗示了大尺度模型是由大家所一起製作的關係。
雖然不一定工作空間在四周的人,一定會參與這個模型的製作,然而因為每次進出都會看到這個大模型,各種設計會議的進行就在身邊,每天都會看到模型製作的新進展等,都容易讓人有參與製作的感覺。對於實際參與製作的人來說,他們工作的合作協調,是在眾目睽睽下進行,這意味著對於與他人之間的不協調感所產生的挫折與怒氣,必須被自我控制。因此在模型製作過程中反思與他人如何協調,就成了田中央事務所生活的重要部分。練習合作,讓工作者更能控制自己的行動,輕鬆自如地與他人相處,這是成就一個優秀匠人的根本要素之一。除了有助於個人技藝的發展外,大尺度模型製作也是事務所內部共同體感受創造的重要途徑之一,因為每個人都因此有了類似的身體經驗,由此可以感受他人的挫折和缺陷,並相互幫助。
就如桑內特所分析的那樣,合作幾乎是人類天生的身體經驗,否則我們將無法用手拿東西,甚至連走路都有困難,因為這些動作,都是靠身體各部位的合作協調才能完成。但當我們與他人協調工作時,卻少反思自己已經存在的身體經驗,合作的能力因此成為一種無用的潛能。一旦我們能反思自己的身體經驗,與他人協作就會較不困難。當我們運用身體經驗來思考如何與他人的合作時,桑內特以手的使用為例建議,人們未必要技能相當才能合作,反而常是因為我們認識到自身的缺點,為了彌補這些缺點,讓工作進行得更完善,才和他人合作。因此,人的不完美,以及深切認識到自身的不完美,是促使我們和諧地和他人合作的重要因素。
今日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田中央的作品之中,都包含了上述這些匠藝。而他們長時間、一改再改、一點也稱不上完美、因為不斷修修補補而顯得有點醜陋的大尺度模型,具體表徵了這些匠藝。就如赫菲斯特斯神話反映了我們一般,在黃聲遠的建築製作中,製作的過程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清楚我們自己是誰?而非僅是完成令人稱羨的作品。
黃聲遠並不是那種技巧卓越臻於完美,讓常人感到望塵莫及的「大師」,也不是汲汲營營於形式風格的創造,想要屢達創作高峰藝術家般的建築師。這些都不是他將建築視為製作的宗旨。透過猶如匠人般的建築師角色,他想探討的是,身為一位跟常人並無二異的建築師,能為環境和公眾做些什麼?長久以來,他堅持於此,就如赫菲斯特斯一般,期盼自己的匠藝,能為自己能觸及到的人帶來和平與自由,並以此來反照自身的生命經驗,就如本文開頭所引黃聲遠的〈自由城市〉裡所述說的。他的自由,來自工作與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工作形成了他特殊的生活方式,工作裡的技藝,成了他看待世界的觀點。技藝,或說匠藝,除了技術的精湛掌握外,也包含了施用這些技術背後的價值觀。因此一味地握緊技術,想以此臻於完美的建築師,不完全是真正的建築師。直面自己經歷過的事實,不崇尚抽象的建築理論,永遠把自身以外的經驗做為參考,而非抄襲;從事實出發,拚命探索在「事實之後」隱含在事實之中的真實,在這個真實的範疇中精進;又能認識到這個自己悟識的真實的極為有限,好奇於別人的真實,但又能保持自主。這或許是黃聲遠的匠藝給我們的啟示。
本文作者│王俊雄
美國康乃爾大學建築碩士,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博士。現任實踐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主授設計,並探險於台灣建築的現代性呈現;且為台灣現代建築學會理事長與《實構築》雜誌總編輯。著有〈中華民國與建築:百年發展歷程〉、〈國民政府時期南京首都計畫之研究〉、〈國民政府時期建築師專業制度之研究〉、〈把現代建築洗出來──洗石子與台灣建築現代性〉等,與徐明松合著《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與王增榮合著《浪漫的真實:戰後蘭陽建築》、與張樞合著《台北原來如此》、與王增榮合編《2014實構築》、與林盛豐和王維仁合編《地域X建築:10個探索》等;其它多篇建築評論,散見於建築專業雜誌。曾參與多項公共空間的規劃與顧問工作,策劃多場建築展覽與OPTOGO米蘭世博外帶台灣館計畫,希望從中尋求身為公民的意義以及從僵化制度中產出自由與美感的可能。目前正策展「田中央歐洲巡迴展」與「2018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
| 1963 | 生於台北 |
| 1978 | 考進建中,漸漸發現自己該念建築 在一片抓施明德「叛亂犯」的宣傳海報中,大家高高興興的排練大會操,拍進看電影前唱國歌的片頭 |
| 1981 | 進東海大學建築系,住宿舍,開始真正和中南部以及東部的同學一起生活 |
| 1982 | 暑假和陳登欽一起第一次到宜蘭 |
| 1983 | 修完洪文雄的構造課,大二暑假和一群同學進行磚砌實構築 大三花很多時間做台灣建築史調查和模型製作,並擔任系學會會長 |
| 1985 | 為了趕送被貓抓傷眼睛的小狗柯布給醫生看,超載被攔,陳登欽和警察「見解不同」,全車被抓進警察局推在牆壁上,陳的手錶碎裂 |
| 1986 | 當兵遇見很多難能可貴的朋友,很懷念那個熱心為我祈福的乩童 |
| 1987 | 解嚴 |
| 1988 | 宗邁工作一年,學習嚴謹的施工圖 |
| 1989 | 進耶魯大學建築研究所 |
| 1990 | 歐洲旅行100天 習作於美國國家建築博物館展出 |
| 1991 | 獲耶魯全院競圖院長獎 畢業 習作選入威尼斯雙年展(美國館) 進洛杉磯Eric Owen Moss事務所工作,做大模型,畫施作圖,衝國際競圖,和全世界來的工讀生交朋友 |
| 1993 | 前往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教書,許多學生入選全國競圖 夏天赴歐洲旅行六週後返台,開始在淡江及華梵教書 |
| 1994 | 成立事務所於宜蘭外員山,黃聲遠睡覺的地方,白天成了跟縣政府人員開會的會議空間,夏天工讀生來時一起睡在同一個大屋頂下。郭文豐是最早的萬能夥伴 |
| 1995 | 事務所搬家,市區公寓裡每人都有一張自己設計又厚又挺的平行尺大桌。起步建立專業的會計制度 |
| 1996 | 開始在中原教書,持續20年 楊志仲加入,成為20多年來田中央最重要的營建工務推手 |
| 1998 | 礁溪林宅獲建築師雜誌獎 學生葉照賢加入,鍛煉往後13年的設計能量 |
| 1999 | 921大地震 竹林養護院/林宅/三星蔥蒜棚獲遠東建築獎傑出建築設計 竹林養護院獲台灣建築獎 |
| 2000 | 蔡東南、王士芳、杜德裕、黃介二、黃致儒、張堂潮、劉崇聖、廖偉伃等幾乎同時進入事務所 |
| 2002 | 事務所第一次離開宜蘭工作,與羅萬照一起完成國慶創意牌樓 |
| 2003 | 開始宜蘭河規劃案 搬到員山鄉惠好村,周圍都是農田水圳的舊成衣廠裡 介入宜興路拓寬規畫,發展出𠲍𠲍噹計畫 擔任阿寶教育基金會發起人 |
| 2004 | 第一次「工讀生之夜」在收割後的稻田裡舉行 宜蘭河畔舊城生活廊帶獲台灣建築獎,會計塗淑娟以非建築人身分,在《建築師》雜誌上發表得獎感言,打動了很多人,「田中央」(台語)一詞第一次公開出現 |
| 2005 | 參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年展,發表「自由城市」 江曜宇第三度回台協助田中央,「工作方法復興運動」開始,1:1細部大樣模型、平行尺重新架設、大量使用手繪圖、模型必需用白膠黏到很牢 宜蘭河畔舊城生活廊帶獲遠東建築獎 至馬來西亞古晉演講 |
| 2006 | 第二次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展場已可由蔡東南帶頭一手搞定 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演講 擔任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共同發起人 獲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 |
| 2008 | 田中央工作群的概念成型,杜德裕任執行長,王士芳推文化事務,白宗弘協調地方,周銘彥發展出行政助理的模式 開始面對宜蘭以外工作的挑戰,在淡水設辦公室構思雲門新家 參加第二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年展 江國梁導演開拍田中央紀錄片 羅東新林場獲台灣建築獎 |
| 2009 | 連續輸掉宜蘭河跟清大宜蘭校區競圖 至印度孟買演講 |
| 2010 | 搬入縣政中心附近的田中央工作場 櫻花陵園獲WA《世界建築》雜誌年度最佳建築 |
| 2011 | 得子口溪及噶瑪蘭水路研究啟動,用夾板製作獨木舟試航成功 參加成都雙年展 擔任成功大學駐校建築師 至新加坡大學及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演講 江國梁發表《黃聲遠在田中央》紀錄片 |
| 2012 | 羅東文化工場獲中國建築傳媒獎最佳建築獎 經長期整合,終於推動「加留沙埔」及「壯圍歸真」的環境概念成為地方共識 至香港大學專題演講 |
| 2013 | 維管束計畫獲聯合國宜居城市競賽「建築組」金獎第一名 第一次個展《田中央.工作中》在台北東區展出 東京森美術館邀請黃聲遠在Innovative City論壇演講 受邀至印度香第葛演講並擔任全國畢業競圖決選主審 獲《華爾街日報》年度創意人物 |
| 2014 | 羅東文化工場獲遠東建築獎台灣傑出獎 劉黃謝堯將「五結焚化爐灰渣大型倉儲」調整為「以軟材料暫時包覆」的方案,以修復海岸沙丘地理 |
| 2015 | 田中央第一次國外個展在東京Gallery MA開展,陳立晟協助日本TOTO出版《Living in Place》專書編輯 擔任政治大學駐校藝術家 |
| 2016 | 開始在新竹市工作,老鳥洪于翔、陳哲生留學回國後帶領年輕夥伴投入 田中央歐洲巡迴展啟動,首站在芬蘭Alvar Aalto博物館 擔任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年展閉幕Keynote Speaker |
| 2017 | 田中央歐洲巡迴展到愛沙尼亞、捷克Ostrava、波蘭及布拉格展出,張文睿不斷累積跨國策展經驗 大塊文化出版《在田中央》故事書 至印度Jaipur演講 赴挪威科技大學及挪威建築師公會演講 雲門劇場獲遠東建築獎台灣傑出獎 |
| 2018 | 獲頒第二十屆國家文藝獎 |